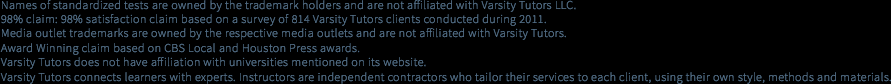例子问题
问题1:人文文章中作者观点与信仰的推论
缅甸是东南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克伦”这个名字是缅甸20多个亚民族的统称,它们构成了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克伦人流离失所,被迫以难民身份生活在泰国,在那里他们没有公民权和基本人权。历史上,缅甸的暴力迫使克伦人进入缅甸东部高地,在那里许多人因信仰基督教而受到迫害。克伦人的一些成员遭受酷刑,而另一些则被迫成为奴隶。今天,克伦人仍在努力从许多层面上——包括语言层面上——摆脱他们动荡的历史。
“卡伦”一词的起源有争议。《牛津词典》指出,“克伦”一词来源于缅甸语“ka-reng”,意思是“野蛮、不洁的人”。然而,“克伦”一词的缅甸语词源究竟是“ka-reng”还是“kayin”,目前还不清楚。克伦族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尼克·吉士曼(Nick Cheesman)认为,“克伦”是缅甸语“kayin”的英语化,其直接翻译是未知的。一种说法是,“kayin”的意思是“土著人”,但另一种说法是“山上的野牛”。
牛津词典并没有解释“Karen”词源上的歧义,反而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它对“克伦”这个词的代表一直是克伦人痛苦的根源,他们讨厌自己被描述为“野蛮、不洁的人”。克伦人已经遭受了许多动乱和压迫;对他们身份起源的刻画只会加深他们的困境。
鉴于“Karen”一词的起源不确定,以及《牛津词典》目前给克伦人带来的痛苦,一些活动人士敦促《牛津词典》将“Karen”一词的来源从“野蛮、不洁的人”改为“土著人”。“土著人”这个词与“野蛮、不洁的人”同样准确,甚至更准确,而且不会冒犯它试图描述的民众。然而,推动变革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努力。对于《牛津词典》来说,承认它在定义上有错误可能会让它受到审查。然而,在允许克伦人继续受苦和承认错误这两种选择之间,后者更为良性。
作者很可能认为,牛津词典对克伦人的定义源于:
缺乏彻底的研究
关于选择最佳定义的智力讨论
在语言辩论中选择站队
支持缅甸多数人统治的政治暗示
对克伦人的恶意
缺乏彻底的研究
鉴于作者提供了关于“Karen”这个词的真实来源的确凿信息,这意味着牛津词典在发布定义之前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
问题21:从人文文章中推断
缅甸是东南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克伦”这个名字是缅甸20多个亚民族的统称,它们构成了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克伦人流离失所,被迫以难民身份生活在泰国,在那里他们没有公民权和基本人权。历史上,缅甸的暴力迫使克伦人进入缅甸东部高地,在那里许多人因信仰基督教而受到迫害。克伦人的一些成员遭受酷刑,而另一些则被迫成为奴隶。今天,克伦人仍在努力从许多层面上——包括语言层面上——摆脱他们动荡的历史。
“卡伦”一词的起源有争议。《牛津词典》指出,“克伦”一词来源于缅甸语“ka-reng”,意思是“野蛮、不洁的人”。然而,“克伦”一词的缅甸语词源究竟是“ka-reng”还是“kayin”,目前还不清楚。克伦族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尼克·吉士曼(Nick Cheesman)认为,“克伦”是缅甸语“kayin”的英语化,其直接翻译是未知的。一种说法是,“kayin”的意思是“土著人”,但另一种说法是“山上的野牛”。
牛津词典并没有解释“Karen”词源上的歧义,反而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它对“克伦”这个词的代表一直是克伦人痛苦的根源,他们讨厌自己被描述为“野蛮、不洁的人”。克伦人已经遭受了许多动乱和压迫;对他们身份起源的刻画只会加深他们的困境。
鉴于“Karen”一词的起源不确定,以及《牛津词典》目前给克伦人带来的痛苦,一些活动人士敦促《牛津词典》将“Karen”一词的来源从“野蛮、不洁的人”改为“土著人”。“土著人”这个词与“野蛮、不洁的人”同样准确,甚至更准确,而且不会冒犯它试图描述的民众。然而,推动变革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努力。对于《牛津词典》来说,承认它在定义上有错误可能会让它受到审查。然而,在允许克伦人继续受苦和承认错误这两种选择之间,后者更为良性。
作者最有可能同意以下哪一种说法?
《牛津词典》对“克伦人”的定义是隐喻克伦人在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压迫。
像克伦人所遭受的那样的宗教迫害是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之一。
学术辩论是澄清复杂问题的最佳手段。
尽管《牛津词典》对克伦人的定义是伤害,但与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其他形式的痛苦相比,这就相形见绌了。
“野蛮、不洁净的人”这个短语可能只对克伦人有冒犯性
《牛津词典》对“克伦人”的定义是隐喻克伦人在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压迫。
作者同情克伦人,并将牛津词典中的定义描述为他们受压迫的另一种表现。因此,最好的答案是:
《牛津词典》对“克伦人”的定义是隐喻克伦人在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压迫。
问题1:在人文文章中进行推理
改编自最后的人玛丽·雪莱(1826)
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我看到了卡拉扎。他有些吃惊;他说,他会看看能做些什么,但这需要时间,雷蒙德命令我在中午之前回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影响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呆到第二天,或者在把目前的情况报告给将军之后再回来。我的选择很容易做出。一种不安,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一种对雷蒙德意图的怀疑,促使我立即回到他的住处。离开七塔,我向东骑向甜水河。我选择了一条迂回的小路,主要是为了登上前面提到的山顶,在那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景色。 I had my glass with me. The city basked under the noon-day sun, and the venerable walls formed its picturesque boundary. Immediately before me was the Top Kapou, the gate near which Mahomet had made the breach by which he entered the city. Trees gigantic and aged grew near; before the gate I discerned a crowd of moving human figures—with intense curiosity I lifted my glass to my eye. I saw Lord Raymond on his charger; a small company of officers had gathered about him, and behind was a promiscuous concourse of soldiers and subalterns, their discipline lost, their arms thrown aside; no music sounded, no banners streamed. The only flag among them was one which Raymond carried; he pointed with it to the gate of the city. The circle round him fell back. With angry gestures he leapt from his horse, and seizing a hatchet that hung from his saddle-bow, went with the apparent intention of battering down the opposing gate. A few men came to aid him; their numbers increased; under their united blows the obstacle was vanquished, gate, portcullis, and fence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wide sun-lit way, leading 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now lay open before them. The men shrank back; they seemed afraid of what they had already done, and stood as if they expected some Mighty Phantom to stalk in offended majesty from the opening. Raymond sprung lightly on his horse, grasped the standard, and with words which I could not hear (but his gestures, being their fit accompaniment, were marked by passionate energy), he seemed to adjure their assistance and companionship; even as he spoke, the crowd receded from him. Indignation now transported him; his words I guessed were fraught with disdain—then turning from his coward followers, he addressed himself to enter the city alone. His very horse seemed to back from the fatal entrance; his dog, his faithful dog, lay moaning and supplicating in his path—in a moment more, he had plunged the rowels into the sides of the stung animal, who bounded forward, and he, the gateway passed, was galloping up the broad and desert street.
在此之前,我的灵魂只在我的眼睛里。我惊奇地凝视着,夹杂着恐惧和热情。后一种感觉现在占了主导地位。我忘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要和你一起去,雷蒙德!”我叫了起来,但是,我的眼睛离开了镜子,我几乎看不清离我大约一英里远的人群中矮小的身影,他们围着大门。雷蒙德的形象消失了。我急不可待,用鞭策的力量和松开的缰绳催促我的马下坡,这样,在危险到来之前,我就可以走到我高贵的、神一般的朋友身边了。当我到达平原时,许多建筑物和树木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这座城市。但就在这时,听到了一声撞击声。雷鸣般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中,天空一片漆黑。 A moment more and the old walls again met my sight, while over them hovered a murky cloud; fragments of buildings whirled above, half seen in smoke, while flames burst out beneath, and continued explosions filled the air with terrific thunders. Flying from the mass of falling ruin which leapt over the high walls, and shook the ivy towers, a crowd of soldiers made for the road by which I came; I was surrounded, hemmed in by them, unable to get forward. My impatience rose to its utmost; I stretched out my hands to the men; I conjured them to turn back and save their General, the conqueror of Stamboul, the liberator of Greece; tears, aye tears, in warm flow gushed from my eyes—I would not believe in his destruction, yet every mass that darkened the air seemed to bear with it a portion of the martyred Raymond. Horrible sights were shaped to me in the turbid cloud that hovered over the city; and my only relief was derived from the struggles I made to approach the gate. Yet when I affected my purpose, all I could discern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massive walls was a city of fire: the open way through which Raymond had ridden was enveloped in smoke and flame. After an interval the explosions ceased, but the flames still shot up from various quarters; the dome of St. Sophia had disappeared. Strange to say (the result perhaps of the concussion of air occasioned by the blowing up of the city), huge, white thunder clouds lifted themselves up from the southern horizon, and gathered overhead; they were the first blots on the blue expanse that I had seen for months, and amidst this havoc and despair they inspired pleasure. The vault above became obscured, lightning flashed from the heavy masses, followed instantaneously by crashing thunder; then the big rain fell. The flames of the city bent beneath it, and the smoke and dust arising from the ruins was dissipated.
文章提供的证据表明,作者最有可能同意以下哪一种建议?
雷蒙德是希望的象征。
所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
雷蒙德是个被诽谤的人物。
雷蒙德的死无可避免。
雷蒙德本打算成为这部剧的主角。
雷蒙德的死无可避免。
我们无法从文章中推断出作者的感受,因为它是通过叙述者的眼睛写的。除非我们假设叙述者的偏见是为了代表作者的偏见,否则我们不能有把握地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声明,说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共识,即“所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我们知道雷蒙德不是一个“被诽谤的人物”,因为他受到叙述者的钦佩。雷蒙德显然不是“希望的象征”,因为这篇文章描绘了他的死亡。我们知道“主角”是叙述者,因为他或她的行为在文章开头就被考虑在内。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说雷蒙德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开头之前就决定通过他的死亡来使用雷蒙德这个角色作为一个象征。他的死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了一个强大而坚强的性格进入了一个无法控制的死亡。
问题1:人文文章中作者观点与信仰的推论
改编自最后的人玛丽·雪莱(1826)
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我看到了卡拉扎。他有些吃惊;他说,他会看看能做些什么,但这需要时间,雷蒙德命令我在中午之前回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影响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呆到第二天,或者在把目前的情况报告给将军之后再回来。我的选择很容易做出。一种不安,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一种对雷蒙德意图的怀疑,促使我立即回到他的住处。离开七塔,我向东骑向甜水河。我选择了一条迂回的小路,主要是为了登上前面提到的山顶,在那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景色。 I had my glass with me. The city basked under the noon-day sun, and the venerable walls formed its picturesque boundary. Immediately before me was the Top Kapou, the gate near which Mahomet had made the breach by which he entered the city. Trees gigantic and aged grew near; before the gate I discerned a crowd of moving human figures—with intense curiosity I lifted my glass to my eye. I saw Lord Raymond on his charger; a small company of officers had gathered about him, and behind was a promiscuous concourse of soldiers and subalterns, their discipline lost, their arms thrown aside; no music sounded, no banners streamed. The only flag among them was one which Raymond carried; he pointed with it to the gate of the city. The circle round him fell back. With angry gestures he leapt from his horse, and seizing a hatchet that hung from his saddle-bow, went with the apparent intention of battering down the opposing gate. A few men came to aid him; their numbers increased; under their united blows the obstacle was vanquished, gate, portcullis, and fence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wide sun-lit way, leading 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now lay open before them. The men shrank back; they seemed afraid of what they had already done, and stood as if they expected some Mighty Phantom to stalk in offended majesty from the opening. Raymond sprung lightly on his horse, grasped the standard, and with words which I could not hear (but his gestures, being their fit accompaniment, were marked by passionate energy), he seemed to adjure their assistance and companionship; even as he spoke, the crowd receded from him. Indignation now transported him; his words I guessed were fraught with disdain—then turning from his coward followers, he addressed himself to enter the city alone. His very horse seemed to back from the fatal entrance; his dog, his faithful dog, lay moaning and supplicating in his path—in a moment more, he had plunged the rowels into the sides of the stung animal, who bounded forward, and he, the gateway passed, was galloping up the broad and desert street.
在此之前,我的灵魂只在我的眼睛里。我惊奇地凝视着,夹杂着恐惧和热情。后一种感觉现在占了主导地位。我忘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要和你一起去,雷蒙德!”我叫了起来,但是,我的眼睛离开了镜子,我几乎看不清离我大约一英里远的人群中矮小的身影,他们围着大门。雷蒙德的形象消失了。我急不可待,用鞭策的力量和松开的缰绳催促我的马下坡,这样,在危险到来之前,我就可以走到我高贵的、神一般的朋友身边了。当我到达平原时,许多建筑物和树木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这座城市。但就在这时,听到了一声撞击声。雷鸣般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中,天空一片漆黑。 A moment more and the old walls again met my sight, while over them hovered a murky cloud; fragments of buildings whirled above, half seen in smoke, while flames burst out beneath, and continued explosions filled the air with terrific thunders. Flying from the mass of falling ruin which leapt over the high walls, and shook the ivy towers, a crowd of soldiers made for the road by which I came; I was surrounded, hemmed in by them, unable to get forward. My impatience rose to its utmost; I stretched out my hands to the men; I conjured them to turn back and save their General, the conqueror of Stamboul, the liberator of Greece; tears, aye tears, in warm flow gushed from my eyes—I would not believe in his destruction, yet every mass that darkened the air seemed to bear with it a portion of the martyred Raymond. Horrible sights were shaped to me in the turbid cloud that hovered over the city; and my only relief was derived from the struggles I made to approach the gate. Yet when I affected my purpose, all I could discern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massive walls was a city of fire: the open way through which Raymond had ridden was enveloped in smoke and flame. After an interval the explosions ceased, but the flames still shot up from various quarters; the dome of St. Sophia had disappeared. Strange to say (the result perhaps of the concussion of air occasioned by the blowing up of the city), huge, white thunder clouds lifted themselves up from the southern horizon, and gathered overhead; they were the first blots on the blue expanse that I had seen for months, and amidst this havoc and despair they inspired pleasure. The vault above became obscured, lightning flashed from the heavy masses, followed instantaneously by crashing thunder; then the big rain fell. The flames of the city bent beneath it, and the smoke and dust arising from the ruins was dissipated.
这篇文章的作者最有可能不同意以下哪一种说法?
雷蒙德愿意在别人不愿行动的时候采取行动,这是象征性的。
雷蒙德对动物很残忍。
雷蒙德是英雄崇拜的对象。
雷蒙德和叙述者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关系。
雷蒙德知道他进城后可能会死。
雷蒙德对动物很残忍。
对于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确定作者可能完全同意或部分同意。显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作者在谈论文学作品时可能会同意什么,但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一些假设。我们可以假设作者有意通过叙述者对雷蒙德的英雄崇拜,叙述者和雷蒙德之间存在着某种兄弟般的联系。我们可以说,由于他的追随者,他的马和他的狗的犹豫,雷蒙德可能知道进入城市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他这样做,他可能会死。最后,我们可以说,当周围的人不确定或退缩时,雷蒙德愿意坚持下去,这一事实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们也可以说,雷蒙德通常不太可能对动物残忍,尽管他确实踢了他的马,敦促它跑进城市。雷蒙德的狗被描述为“他忠实的狗”这一事实表明,虐待动物不是雷蒙德的正常行为,否则这只狗就没有理由对他忠诚。
问题1:人文文章中作者观点与信仰的推论
改编自引言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Crevecoeur;1782)作者:沃伦·巴顿·布莱克(1912)
除了归化,作者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他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然而,为什么要和他争论他的书的名字,或者他的签名“j·赫克托耳·圣约翰”,当他的标题页和美国传记作家的“赫克托耳”只是一个Prenom de fintaisie?我们应该对十八世纪的梭罗这位如此迷人的作者做出一些让步。他的生活当然比真正的梭罗更有趣,即使没有很多矛盾,也会更有趣。我们对那段生活的记录是极不准确的;他自己对不止一件事的日期也不太准确。然而,记录却表明,克罗蒂弗科尔属于诺曼底的小贵族。他的出生日期是1735年1月31日,出生地是卡昂,他的全名是米歇尔-纪尧姆-让·德·克里弗科尔(他的曾孙和传记作者为他作了证明)。这孩子被抚养得很好,但除了生来就应该得到的关注之外,他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他在卡昂和蒙特学院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卡昂是他父亲的联排别墅所在的地方,而蒙特学院是耶稣会士让他接受教育的地方。一封1785年写给他孩子们的信告诉了我们关于他学生时代的一切; though it is said, too, that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in mathematics. "If you only knew," the reminiscent father of a family exclaims in this letter, "in what shabby lodging, in what a dark and chilly closet, I was mewed up at your age; with what severity I was treated; how I was fed and dressed!" Already his powers of observation, that were so to distinguish him, were quickened by his old-world milieu.
“从我最年轻的时候,”他在1803年写道,“我就热衷于收藏我遇到的所有古董:虫蛀的家具、挂毯、全家福、哥特式手稿(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解读)对我来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不久之后,我喜欢在幽静的墓地里散步,细看坟墓,追寻长满青苔的墓志铭。我知道这个州的大多数教堂,知道它们建立的日期,也知道里面有什么有趣的图画和雕塑。”
不久,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物体将考验这孩子的准确而敏锐的观察力。在美国的森林里,不会有摇摇欲坠的圣像和卧室的油画供他研究,不会有让他想起他的国家过去的伟大和他的家族的光荣的东西。
从学校毕业后,这位未来的樵夫来到了英国。一个远房亲戚住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男孩被送到那里去完成他的学业。我们不知道他从英国出发前往新大陆的动机是什么,他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忙碌、最幸福的日子。里奇在《新美国图书馆》中说,克罗弗里科尔跳下去的时候只有16岁,其他人也跟他一样犯了这个错误。这小伙子的年龄实际上不少于十九、二十岁。根据这个家族的传说,他的船在离开时在里斯本停靠;人们无法确定这是发生在大地震之前还是之后。然后去了新法兰西,在那里他加入了蒙特卡姆。他以军校学员的身份入伍,晋升到中尉军衔; was mentioned in the Gazette; shared in the French successes; drew maps of the forests and block-houses that found their way to the king's cabinet; served with Montcalm in the attack upon Fort William Henry. With that the record is broken off: we can less definitely associate his name with the humiliation of the French in America than with their brief triumphs. Yet it is quite certain, says Robert de Crèvecoeur, his descendant, that he did not return to France with the rag-tag of the defeated army. Quebec fell before Wolfe's attack in September 1759; at some time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1760 we may suppose the young officer to have entered the British colonies, to have adopted his family name of "Saint John" (Saint-Jean), and to have gradually worked his way south, probably by the Hudson. The reader of the信很难想象他喜欢他的边疆生活;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这种生活有多少是幸运的。最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南下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他访问了希本斯堡、兰开斯特和卡莱尔;也许他就住在这些城镇里或附近。许多年后,当他的儿子路易斯在蓝山附近的纳维辛克从利文斯通财政大臣那里买下了一个200英亩的农场时,老克罗维特科尔仍然被人们记得,也许就是在这个时代,他去过那个地方。在蒙特卡姆的军旅生涯中,克罗弗科尔对大湖和边远地区略为了解;在他成为一名种植者之前,事实上,在他成为一名种植者之后,他“像柏拉图一样旅行”,甚至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去过百慕大。然而,直到1764年,我们才有了他行踪的确凿证据;那一年的4月,他在纽约拿出了入籍文件。 Some months later, he installed himself on the farm variously called Greycourt and Pine-Hill, in the same state; he drained a great marsh there, and seems to have practiced agriculture upon a generous scale. The certificate of the marriage of Crèvecoeur to Mehitable Tippet, of Yonkers is dated September 20, 1769, and of this union three children were the issue. And more than children: for with the marriage ceremony once performed by the worthy Tetard, a clergyman of New York, formerly settled over a French Reformed Church at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Crèvecoeur is more definitely than ever the "American Farmer"; he has thrown in his lot with that new country; his children are to be called after their parent's adopted name, Saint-Joh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dventurer are multiplied; his life in America has become a matter more easy to trace and richer, perhaps, in meaning.
文章提供的证据表明,作者最有可能同意以下哪一种建议?
cravevecoeur的婚姻是他转变为他在书名中所暗示的人的最终点。
在克罗维特科的一生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归因于他作为作家的才能。
如果克里弗尔没有从欧洲移民过来,他会过得更好。
在所有促使克里弗尔成为重要文学贡献者的时刻中,最重要的是他年轻时习惯的形成。
克里维特科尔不应该在他的书的标题中使用“美国人”这个词。
cravevecoeur的婚姻是他转变为他在书名中所暗示的人的最终点。
作者在最后一段中相当坚定地指出,cr
问题1:人文文章中作者观点与信仰的推论
改编自引言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Crevecoeur;1782)作者:沃伦·巴顿·布莱克(1912)
除了归化,作者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他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然而,为什么要和他争论他的书的名字,或者他的签名“j·赫克托耳·圣约翰”,当他的标题页和美国传记作家的“赫克托耳”只是一个Prenom de fintaisie?我们应该对十八世纪的梭罗这位如此迷人的作者做出一些让步。他的生活当然比真正的梭罗更有趣,即使没有很多矛盾,也会更有趣。我们对那段生活的记录是极不准确的;他自己对不止一件事的日期也不太准确。然而,记录却表明,克罗蒂弗科尔属于诺曼底的小贵族。他的出生日期是1735年1月31日,出生地是卡昂,他的全名是米歇尔-纪尧姆-让·德·克里弗科尔(他的曾孙和传记作者为他作了证明)。这孩子被抚养得很好,但除了生来就应该得到的关注之外,他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他在卡昂和蒙特学院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卡昂是他父亲的联排别墅所在的地方,而蒙特学院是耶稣会士让他接受教育的地方。一封1785年写给他孩子们的信告诉了我们关于他学生时代的一切; though it is said, too, that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in mathematics. "If you only knew," the reminiscent father of a family exclaims in this letter, "in what shabby lodging, in what a dark and chilly closet, I was mewed up at your age; with what severity I was treated; how I was fed and dressed!" Already his powers of observation, that were so to distinguish him, were quickened by his old-world milieu.
“从我最年轻的时候,”他在1803年写道,“我就热衷于收藏我遇到的所有古董:虫蛀的家具、挂毯、全家福、哥特式手稿(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解读)对我来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不久之后,我喜欢在幽静的墓地里散步,细看坟墓,追寻长满青苔的墓志铭。我知道这个州的大多数教堂,知道它们建立的日期,也知道里面有什么有趣的图画和雕塑。”
不久,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物体将考验这孩子的准确而敏锐的观察力。在美国的森林里,不会有摇摇欲坠的圣像和卧室的油画供他研究,不会有让他想起他的国家过去的伟大和他的家族的光荣的东西。
从学校毕业后,这位未来的樵夫来到了英国。一个远房亲戚住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男孩被送到那里去完成他的学业。我们不知道他从英国出发前往新大陆的动机是什么,他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忙碌、最幸福的日子。里奇在《新美国图书馆》中说,克罗弗里科尔跳下去的时候只有16岁,其他人也跟他一样犯了这个错误。这小伙子的年龄实际上不少于十九、二十岁。根据这个家族的传说,他的船在离开时在里斯本停靠;人们无法确定这是发生在大地震之前还是之后。然后去了新法兰西,在那里他加入了蒙特卡姆。他以军校学员的身份入伍,晋升到中尉军衔; was mentioned in the Gazette; shared in the French successes; drew maps of the forests and block-houses that found their way to the king's cabinet; served with Montcalm in the attack upon Fort William Henry. With that the record is broken off: we can less definitely associate his name with the humiliation of the French in America than with their brief triumphs. Yet it is quite certain, says Robert de Crèvecoeur, his descendant, that he did not return to France with the rag-tag of the defeated army. Quebec fell before Wolfe's attack in September 1759; at some time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1760 we may suppose the young officer to have entered the British colonies, to have adopted his family name of "Saint John" (Saint-Jean), and to have gradually worked his way south, probably by the Hudson. The reader of the信很难想象他喜欢他的边疆生活;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这种生活有多少是幸运的。最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南下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他访问了希本斯堡、兰开斯特和卡莱尔;也许他就住在这些城镇里或附近。许多年后,当他的儿子路易斯在蓝山附近的纳维辛克从利文斯通财政大臣那里买下了一个200英亩的农场时,老克罗维特科尔仍然被人们记得,也许就是在这个时代,他去过那个地方。在蒙特卡姆的军旅生涯中,克罗弗科尔对大湖和边远地区略为了解;在他成为一名种植者之前,事实上,在他成为一名种植者之后,他“像柏拉图一样旅行”,甚至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去过百慕大。然而,直到1764年,我们才有了他行踪的确凿证据;那一年的4月,他在纽约拿出了入籍文件。 Some months later, he installed himself on the farm variously called Greycourt and Pine-Hill, in the same state; he drained a great marsh there, and seems to have practiced agriculture upon a generous scale. The certificate of the marriage of Crèvecoeur to Mehitable Tippet, of Yonkers is dated September 20, 1769, and of this union three children were the issue. And more than children: for with the marriage ceremony once performed by the worthy Tetard, a clergyman of New York, formerly settled over a French Reformed Church at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Crèvecoeur is more definitely than ever the "American Farmer"; he has thrown in his lot with that new country; his children are to be called after their parent's adopted name, Saint-Joh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dventurer are multiplied; his life in America has become a matter more easy to trace and richer, perhaps, in meaning.
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__________.
克伦维特科是一位重要的作家,比他之后一个世纪的一些作家更重要。
cravevecoeur的一生很有趣。
crevevecoeur可以被看作是农民、冒险家、丈夫和樵夫。
克里弗尔对周围的环境很有洞察力。
crevevecoeur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是在1759年。
crevevecoeur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是在1759年。
使这句话明显与作者的断言相反的是,它非常具体。如果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肯定其他的说法。例如,“克罗维托尔对周围的环境有敏锐的观察力”,这句话有一句支持,“他的观察力,使他与众不同,已经因为他的旧世界的环境而增强了。”然而,如果我们在文本中搜索1759年的日期,我们就会发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后代罗伯特·德·克罗特维科说,“他并没有带着败军的乌合之众回到法国。”魁北克在1759年9月沃尔夫进攻之前就沦陷了。”诚然,克罗维特科留在美国的决定很重要,但作者不会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作者在文章中非常坚定地认为,cr
问题7:在人文文章中进行推理
改编自英雄与英雄崇拜托马斯·卡莱尔(1841)。
作为神的英雄,作为先知的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不会在新时代重复。它们以某种粗陋的观念为前提,这种观念被单纯的科学知识的进步所终结。如果人们在充满爱的惊奇中把他们的同胞想象成一个神,或者一个用神的声音说话的人,那么,必须有一个空虚的,或者几乎是空虚的科学形式的世界。神和先知都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英雄是诗人,他的品格不那么雄心勃勃,但也不那么值得怀疑;不通过的字符。诗人是属于所有时代的英雄人物;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一旦他被创造出来,最新的时代就像最古老的时代一样可以创造他,而且只要自然愿意,他就会创造出来。让大自然送出一个英雄的灵魂;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把他塑造成诗人。
英雄、先知、诗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我们给伟人取了许多不同的名字;根据我们在它们身上看到的种类,根据它们展示自己的领域!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给出更多的名字。然而,我要再次指出,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同之处在于球构成这种区别的伟大起源;英雄可以是诗人,先知,国王,牧师,或者你想要的,这取决于他发现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世界。我承认,我不认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可能的所有各种各样的男人。只会坐在椅子上写诗节的诗人,永远不会写出有多大价值的诗节。他不会唱《英勇的战士》,除非他自己至少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我猜想他身上有政治家、思想家、立法者和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是,他是所有这些人。我也不明白,一个米拉波,他那颗伟大的心,那颗火,那颗泪,怎么就写不出诗、悲剧、诗歌,那样打动所有人的心,他的人生历程和受的教育,怎么能把他带到那里去呢?伟大的基本性格是伟人的性格;这个人是伟大的。拿破仑说的话就像奥斯特里茨战役。路易十四的元帅们是一种富有诗意的人;杜伦的话充满了睿智和亲切,就像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一样。 The great heart, the clear deep-seeing eye: there it lies; no man whatever, in what province soever, can prosper at all without these. Petrarch and Boccaccio did diplomatic messages, it seems, quite well; one can easily believe it; they had done things a little harder than these! Burns, a gifted song-writer, might have made a still better Mirabeau. Shakespeare—one knows not what他绝对不可能做到。
诚然,大自然也有天资。大自然并不是用同样的模子造就伟大的人。无疑是天资的不同,但更多的是环境的不同后者我们只关注这些。但这就像普通人学习手艺一样。你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能力还很模糊,他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工匠,把他变成一个铁匠,一个木匠,一个泥瓦匠;从那时起,他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如果像艾迪生抱怨的那样,你有时看到一个搬运工,拄着纺锤柄,摇摇晃晃地扛着担子,而在你的近旁有一个裁缝,身板像参孙一样,手里拿着一块布和一根白教堂的小针,那么,你也不能认为这仅仅是请教了大自然的才能!伟大的人,他要做什么学徒呢?给定你的英雄,他会成为征服者、国王、哲学家、诗人吗?这是世界和他之间一场莫名其妙的复杂的、有争议的算计!他将阅读世界和世界的法则;世界和它的法则将在那里被阅读。 What the world, on这正如我们所说的,物质允许并允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实。
诗人和先知在我们松散的现代观念中差别很大。在一些古老的语言中,同样,标题是同义的;“Vates”意味着两者先知和诗人;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先知和诗人,如果被很好地理解,都有许多相似的含义。从根本上说,它们仍然是一样的;特别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已经把这两者都渗透进了宇宙的神圣神秘之中;歌德称之为“公开的秘密”。“哪个是最大的秘密?”其中一个问道。“开放秘密,“向所有人开放,却几乎没有人看见!”神圣的神秘,无处不在,存在于一切存在之中,如费希特所说,“世界的神圣理念,存在于现象的底层”;其中所有的表象,从星空到田野的草,尤其是人类的表象和他的工作,都不过是一种表象衣裳即使其可见的化身。这神圣的奥秘是无论何时何地;真正地。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它被大大忽视了;而宇宙,总是用一种或另一种语言来定义,作为上帝的已实现的思想,却被认为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无生气的、司空见惯的东西——讽刺作家说,就好像它是一件死的东西,是某个室内装潢家拼出来的!目前,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说话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了解它,永远生活在它的知识之中,那将是一种遗憾。真是一件最悲哀的憾事——如果我们不这样生活,那就根本不能活着!
文章的作者最有可能提出以下哪一种批评?
认为像参孙那样健壮的人能成为裁缝真是背信弃义。
把彼特拉克这样的人误认为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认为所有伟人都是自然的产物,这是一种谬误。
崇拜英雄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那些愿意否认诗人和先知之间联系的人是在欺骗自己。
那些愿意否认诗人和先知之间联系的人是在欺骗自己。
作者在第四段中说,诗人和先知之间的联系现在可能有所改变,但“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先知和诗人,很好地理解,有很多相似的含义。从根本上说,它们仍然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不应予以否认。叙述者从来没有说过崇拜英雄是愚蠢的。彼得拉克和莎士比亚之间没有比较,叙述者也没有说大自然是伟人的唯一创造者。
问题8:在人文文章中进行推理
改编自英雄与英雄崇拜托马斯·卡莱尔(1841)。
作为神的英雄,作为先知的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不会在新时代重复。它们以某种粗陋的观念为前提,这种观念被单纯的科学知识的进步所终结。如果人们在充满爱的惊奇中把他们的同胞想象成一个神,或者一个用神的声音说话的人,那么,必须有一个空虚的,或者几乎是空虚的科学形式的世界。神和先知都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英雄是诗人,他的品格不那么雄心勃勃,但也不那么值得怀疑;不通过的字符。诗人是属于所有时代的英雄人物;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一旦他被创造出来,最新的时代就像最古老的时代一样可以创造他,而且只要自然愿意,他就会创造出来。让大自然送出一个英雄的灵魂;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把他塑造成诗人。
英雄、先知、诗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我们给伟人取了许多不同的名字;根据我们在它们身上看到的种类,根据它们展示自己的领域!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给出更多的名字。然而,我要再次指出,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同之处在于球构成这种区别的伟大起源;英雄可以是诗人,先知,国王,牧师,或者你想要的,这取决于他发现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世界。我承认,我不认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可能的所有各种各样的男人。只会坐在椅子上写诗节的诗人,永远不会写出有多大价值的诗节。他不会唱《英勇的战士》,除非他自己至少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我猜想他身上有政治家、思想家、立法者和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是,他是所有这些人。我也不明白,一个米拉波,他那颗伟大的心,那颗火,那颗泪,怎么就写不出诗、悲剧、诗歌,那样打动所有人的心,他的人生历程和受的教育,怎么能把他带到那里去呢?伟大的基本性格是伟人的性格;这个人是伟大的。拿破仑说的话就像奥斯特里茨战役。路易十四的元帅们是一种富有诗意的人;杜伦的话充满了睿智和亲切,就像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一样。 The great heart, the clear deep-seeing eye: there it lies; no man whatever, in what province soever, can prosper at all without these. Petrarch and Boccaccio did diplomatic messages, it seems, quite well; one can easily believe it; they had done things a little harder than these! Burns, a gifted songwriter, might have made a still better Mirabeau. Shakespeare—one knows not what他绝对不可能做到。
诚然,大自然也有天资。大自然并不是用同样的模子造就伟大的人。无疑是天资的不同,但更多的是环境的不同后者我们只关注这些。但这就像普通人学习手艺一样。你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能力还很模糊,他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工匠,把他变成一个铁匠,一个木匠,一个泥瓦匠;从那时起,他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如果像艾迪生抱怨的那样,你有时看到一个搬运工,拄着纺锤柄,摇摇晃晃地扛着担子,而在你的近旁有一个裁缝,身板像参孙一样,手里拿着一块布和一根白教堂的小针,那么,你也不能认为这仅仅是请教了大自然的才能!伟大的人,他要做什么学徒呢?给定你的英雄,他会成为征服者、国王、哲学家、诗人吗?这是世界和他之间一场莫名其妙的复杂的、有争议的算计!他将阅读世界和世界的法则;世界和它的法则将在那里被阅读。 What the world, on这正如我们所说的,物质允许并允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实。
诗人和先知在我们松散的现代观念中差别很大。在一些古老的语言中,同样,标题是同义的;“Vates”意味着两者先知和诗人;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先知和诗人,如果被很好地理解,都有许多相似的含义。从根本上说,它们仍然是一样的;特别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已经把这两者都渗透进了宇宙的神圣神秘之中;歌德称之为“公开的秘密”。“哪个是最大的秘密?”其中一个问道。“开放秘密,“向所有人开放,却几乎没有人看见!”神圣的神秘,无处不在,存在于一切存在之中,如费希特所说,“世界的神圣理念,存在于现象的底层”;其中所有的表象,从星空到田野的草,尤其是人类的表象和他的工作,都不过是一种表象衣裳即使其可见的化身。这神圣的奥秘是无论何时何地;真正地。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它被大大忽视了;而宇宙,总是用一种或另一种语言来定义,作为上帝的已实现的思想,却被认为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无生气的、司空见惯的东西——讽刺作家说,就好像它是一件死的东西,是某个室内装潢家拼出来的!目前,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说话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了解它,永远生活在它的知识之中,那将是一种遗憾。真是一件最悲哀的憾事——如果我们不这样生活,那就根本不能活着!
文章的作者最有可能不同意以下哪一种说法?
事物神圣的外表是难以察觉的。
上帝是一个存在于单一地方的单一观念。
我们不应该创造神圣的英雄,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
先知的概念已经过时了。
先知和神被取代了。
上帝是一个存在于单一地方的单一观念。
关于先知和神作为英雄的三个陈述(“先知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我们不应该创造神圣的英雄”,“先知和神已经被取代了”)都在第一段中得到了解决和验证。另外两句话(“事物的神圣外观很难被感知”和“上帝是一个居住在单一地方的单一观念”)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论证,有一个比静态的“神”的刻板形象更伟大的神的存在。想想这些诗句:“这神圣的奥秘是无论何时何地;真正地。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这一点被大大忽视了,而宇宙,总是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来定义,作为上帝的思想的实现,被认为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无生气的、平凡的东西。”这段引文提供了证据,表明作者不同意上帝是一个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单一实体的假设。
问题9:在人文文章中进行推理
改编自英雄与英雄崇拜托马斯·卡莱尔(1841)。
作为神的英雄,作为先知的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不会在新时代重复。它们以某种粗陋的观念为前提,这种观念被单纯的科学知识的进步所终结。如果人们在充满爱的惊奇中把他们的同胞想象成一个神,或者一个用神的声音说话的人,那么,必须有一个空虚的,或者几乎是空虚的科学形式的世界。神和先知都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英雄是诗人,他的品格不那么雄心勃勃,但也不那么值得怀疑;不通过的字符。诗人是属于所有时代的英雄人物;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一旦他被创造出来,最新的时代就像最古老的时代一样可以创造他,而且只要自然愿意,他就会创造出来。让大自然送出一个英雄的灵魂;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把他塑造成诗人。
英雄、先知、诗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我们给伟人取了许多不同的名字;根据我们在它们身上看到的种类,根据它们展示自己的领域!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给出更多的名字。然而,我要再次指出,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同之处在于球构成这种区别的伟大起源;英雄可以是诗人,先知,国王,牧师,或者你想要的,这取决于他发现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世界。我承认,我不认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可能的所有各种各样的男人。只会坐在椅子上写诗节的诗人,永远不会写出有多大价值的诗节。他不会唱《英勇的战士》,除非他自己至少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我猜想他身上有政治家、思想家、立法者和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是,他是所有这些人。我也不明白,一个米拉波,他那颗伟大的心,那颗火,那颗泪,怎么就写不出诗、悲剧、诗歌,那样打动所有人的心,他的人生历程和受的教育,怎么能把他带到那里去呢?伟大的基本性格是伟人的性格;这个人是伟大的。拿破仑说的话就像奥斯特里茨战役。路易十四的元帅们是一种富有诗意的人;杜伦的话充满了睿智和亲切,就像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一样。 The great heart, the clear deep-seeing eye: there it lies; no man whatever, in what province soever, can prosper at all without these. Petrarch and Boccaccio did diplomatic messages, it seems, quite well; one can easily believe it; they had done things a little harder than these! Burns, a gifted songwriter, might have made a still better Mirabeau. Shakespeare—one knows not what他绝对不可能做到。
诚然,大自然也有天资。大自然并不是用同样的模子造就伟大的人。无疑是天资的不同,但更多的是环境的不同后者我们只关注这些。但这就像普通人学习手艺一样。你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能力还很模糊,他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工匠,把他变成一个铁匠,一个木匠,一个泥瓦匠;从那时起,他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如果像艾迪生抱怨的那样,你有时看到一个搬运工,拄着纺锤柄,摇摇晃晃地扛着担子,而在你的近旁有一个裁缝,身板像参孙一样,手里拿着一块布和一根白教堂的小针,那么,你也不能认为这仅仅是请教了大自然的才能!伟大的人,他要做什么学徒呢?给定你的英雄,他会成为征服者、国王、哲学家、诗人吗?这是世界和他之间一场莫名其妙的复杂的、有争议的算计!他将阅读世界和世界的法则;世界和它的法则将在那里被阅读。 What the world, on这正如我们所说的,物质允许并允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实。
诗人和先知在我们松散的现代观念中差别很大。在一些古老的语言中,同样,标题是同义的;“Vates”意味着两者先知和诗人;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先知和诗人,如果被很好地理解,都有许多相似的含义。从根本上说,它们仍然是一样的;特别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已经把这两者都渗透进了宇宙的神圣神秘之中;歌德称之为“公开的秘密”。“哪个是最大的秘密?”其中一个问道。“开放秘密,“向所有人开放,却几乎没有人看见!”神圣的神秘,无处不在,存在于一切存在之中,如费希特所说,“世界的神圣理念,存在于现象的底层”;其中所有的表象,从星空到田野的草,尤其是人类的表象和他的工作,都不过是一种表象衣裳即使其可见的化身。这神圣的奥秘是无论何时何地;真正地。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它被大大忽视了;而宇宙,总是用一种或另一种语言来定义,作为上帝的已实现的思想,却被认为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无生气的、司空见惯的东西——讽刺作家说,就好像它是一件死的东西,是某个室内装潢家拼出来的!目前,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说话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了解它,永远生活在它的知识之中,那将是一种遗憾。真是一件最悲哀的憾事——如果我们不这样生活,那就根本不能活着!
文章提供的证据表明,作者最有可能同意以下哪一种建议?
对英雄的天性是嫉妒。
出身贫寒的人不太可能成为自然所希望他们成为的英雄。
把一个人提升为英雄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重要的是要确定哪些人可能成为合适的英雄,以防止他或她变得默默无闻。
上帝的想法并非不现实;然而,这可能被误解了。
上帝的想法并非不现实;然而,这可能被误解了。
如果我们消除极不可能的语句,如“自然对英雄的性格是嫉妒”或“出生贫困家庭不太可能成为自然需要他们的英雄,”因为他们没有提到的文本或他们提出观点相反,剩下的语句,“这是所有人的利益提升一个人的状态英雄”和“上帝不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这可能被误解了。”在这两者中,关于上帝的陈述被这段话的最后一部分所证实:“这神圣的奥秘是无论何时何地;真正地。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它被大大忽视了;而宇宙,总是用一种或另一种方言来定义,作为上帝的已实现的思想,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惰性的,平凡的物质……”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相信某种形式的神,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解或误解了。
问题10:在人文文章中进行推理
改编自亨利·大卫·梭罗的《行走》(1862)牛津美国散文集(1914)
我希望为自然、为绝对的自由和野性说话,而不是仅仅文明的自由和文化——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居民,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的一员。我想发表一个极端的声明,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发表一个强调的声明,因为文明的捍卫者已经够多了:部长和学校委员会,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照顾到这一点。
在我的一生中,我只遇到过一两个懂得散步的艺术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天才,可以这么说无所事事的这个词源自“中世纪游遍乡间,假借外出之名请求施舍的闲人”圣特雷直到孩子们惊叫道:“那里去了一个。Sainte-Terrer“一个漫步者——一个圣洁的人。那些散步从不去圣地的人,就像他们假装的那样,实际上只是懒汉和流浪汉;但是那些去那里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浪者,就像我所说的那样。然而,有些人会把这个词从无特因此,从好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没有特别的家,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家。因为这是成功漫步的秘诀。整天坐在家里不动的人,也许是最大的流浪者;但是,从好的意义上说,漫步者并不比蜿蜒的河流更流浪,因为它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通往大海的最短路线。但我更喜欢第一种推导,因为它确实是最可能的推导。因为每一次散步都是一种十字军东征,是我们内心某个隐士彼得所宣讲的,要从敌人手中夺回这片圣地。
的确,我们现在不过是懦弱的十字军战士,甚至是行路人,我们没有坚持不懈、永无止境的事业。我们的探险不过是一次旅行,到了晚上又回到我们出发的老炉边。走了一半的路是在走回头路。也许,我们应该怀着永恒的冒险精神,出去走一段最短的路,再也不回来了——准备好把我们经过防腐处理的心,只作为遗物,送回我们荒凉的王国。如果你准备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孩子和朋友,永远不再见到他们——如果你已经还清了债务,立了遗嘱,解决了所有的事务,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么你就可以出去散步了。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的同伴和我,因为我有时有一个同伴,都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新阶层的骑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旧阶层的骑士——不是骑士或骑士,不是骑士或骑士,而是行骑士,我相信这是一个更古老、更光荣的阶层。曾经属于骑士的骑士精神和英雄精神现在似乎存在于行者身上,或者可能已经消退到行者身上——不是骑士,而是游侠。他是教会,国家和人民之外的第四等级。
我们感到,在这一带,几乎只有我们在实践这种高尚的艺术;不过,说实话,至少,如果他们自己的主张被人接受的话,我的城里大多数人有时也愿意像我一样散步,但是他们不能。任何财富都买不到必要的闲暇、自由和独立,而这些是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本。它只能靠上帝的恩典来实现。要成为一个行路的人,需要上天的直接恩赐。你一定出生在沃克家族。救护车,不合适。的确,我的一些同城居民还记得,并向我描述了他们十年前散步的一些事情,在那次散步中,他们很幸运,在树林里迷失了半个小时;但我很清楚,从那以后,他们就把自己局限在公路上了,不管他们怎么自命属于这上等人。毫无疑问,他们一时兴奋起来,仿佛是由于回忆起以前的生活状态,那时连他们自己都是护林员和亡命之徒。
“当他来到绿林的时候,
在一个愉快的早晨,
在那里,他把钞票整理得很小
所有的字节都是同步的。
“它已经消失了,”罗宾说,
我是最后一个来到这里的;
我找了一个lytell来射击
在多恩广场。”
我认为,我无法保持健康和精神,除非我每天至少花四个小时——通常还不止四个小时——信步穿过树林、翻过小山和田野,完全摆脱一切世俗的事务。你可以说:一分钱换你的思想,一千英镑换你的思想。有时我想起机械师和店主不仅整个上午,而且整个下午都呆在店里,盘腿坐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仿佛腿是用来坐的,而不是用来站或走的——我想,他们没有早就自杀,这是值得赞扬的。
文章提供的证据表明作者最有可能同意以下哪一种说法?
步行最好独自进行。
现代步行者是过去步行者的影子。
我们应该在狗身上投资,因为它们会给我们走路的理由。
那些说自己喜欢散步却住在城镇里的人是最大的伪君子。
散步应该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现代步行者是过去步行者的影子。
在第三段中,作者指出,“的确,我们现在不过是懦弱的十字军战士,甚至是步行者,我们没有坚持不懈、永无止境的事业。我们的探险只不过是一次旅行,到了晚上,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出发的老炉边。”因此,这句话使现代步行者看起来只是他们前辈伟大的影子。我们不能说其他任何选项都是正确的,因为作者说有一类人更自然地走路,而且他经常有同伴陪伴。他没有严厉到批评那些住在城镇里的人是伪君子,而关于狗的陈述虽然令人信服,但在文本中缺乏足够的证据。